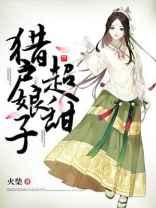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5章 行于天地,再遇自己(3/3)
,路上绕道去看闻名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的圣地——兽主大庙。
大庙所处的地方并不冲要,要走过几条狭窄又不十分干净的小巷子才能到。
尼泊尔的圣河,同印度圣河恒河并称的波特摩瓦底河,流过大庙前面。
在这一条圣河的岸边上建了几个台子,据说是焚烧死人尸体的地方,焚烧剩下的灰就近倾入河中。
这一条河同印度恒河一样,据说是通向天堂的。
骨灰倾入河中,人就上升天堂了。
兽主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,平常被称作湿婆的就是。
湿婆的象征linga,是一个大石柱。
这里既然是湿婆的庙,所以linga也被供在这里,就在庙门外河对岸的一座石头屋子里。
据说,这里的妇女如果不能生孩子,来到linga前面,烧香磕头,然后用手抚摩linga,回去就能怀孕生子。
是不是真这样灵验呢?就只有天知道或者湿婆大神知道了。
庙门口皇皇然立着一个大木牌,上面写着:“非印度教徒严禁入内”。
我们不是印度教徒,当然只能从外面向门内张望一番,然后望望然去之。
庙内并不怎样干净,同小说中描绘的洞天福地迥乎不同,看上去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神圣或神秘的地方。
古人诗说:“凡所难求皆绝好。
”既然无论如何也进不去,只好觉得庙内一切“皆绝好”了。
人们告诉我们,这座大庙在印度也广有名气。
每年到了什么节日,信印度教的印度人不远千里,跋山涉水,到这里来朝拜大神。
我们确实看到了几个苦行僧打扮的人,但不知是否就是从印度来的。
不管怎样,此处是圣地无疑,否则拄竹杖梳辫子的圣人苦行者也不会到这里来流连盘桓了。
说老实话,我从来也没有信过任何神灵。
我对什么神庙,什么善主,什么linga,并不怎么感兴趣。
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另外一些东西,庙中高阁的顶上落满了鸽子。
虽然已近黄昏,暮色从远处的雪山顶端慢慢下降,夕阳残照古庙颓垣,树梢上都抹上了一点金黄。
是鸽子休息的时候了。
但是它们好像还没有完全休息,从鸽群中不时发出了咕咕的叫声。
比鸽子还更引起我的兴趣的是猴子。
房顶上,院墙上,附近居民的屋子上,圣河小桥的栏杆上,到处都是猴,又跳又跃,又喊又叫。
有的老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,或者怀里抱着小猴子,在屋顶与屋顶之间,来来往往,片刻不停。
有的背上驮着一片夕阳,闪出耀眼的金光。
当它们走上桥头的时候,我也正走到那里。
我忽然心血来潮,伸手想摸一下一个小猴。
没想到老猴子绝不退避,而是龇牙咧嘴,抬起爪子,准备向我进攻。
这种突然袭击,真正震慑住了我,我连忙退避三舍,躲到一旁去了。
我忽然灵机一动,想入非非。
我上面已经说到,印度教的庙非印度教徒是严禁入内的。
如果硬往里闯,其后果往往非常严重。
但这只是对人而言,对猴子则另当别论。
人不能进,但是猴子能进。
猴子们大概根本不关心人间的教派、人间的种姓、人间的阶级、人间的官吏,什么法律规章,什么达官显宦,它们统统不放在眼中,而且加以蔑视。
从来也没有什么人把猴子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。
猴子是这样,鸽子也是这样,在所有的国家统统是这样。
猴子们和鸽子们大概认为,人间的这些花样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它们独行独来,天马行空,海阔纵鱼跃,天高任鸟飞,它们比人类要自由得多。
按照一些国家轮回转生的学说,猴子们和鸽子们大概未必真想转生为人吧! 我的幻想实在有点过了头,还是赶快收回来吧。
在人间,在我眼前的兽主大庙门前,人们熙攘往来。
有的衣着讲究,有的浑身褴褛。
苦行者昂首阔步,满面圣气,手拄竹杖,头梳长发,走在人群之中,宛如鸡群之鹤。
卖鲜花的小贩,安然盘腿坐在小铺子里,恭候主顾大驾光临。
高鼻子蓝眼睛满头黄发的外国青年男女,背着书包,站在那里商量着什么。
神牛们也夹在中间,慢慢前进。
讨饭的盲人和小孩子伸手向人要钱。
小铺子里摆出的新鲜的白萝卜等菜蔬闪出了白色的光芒。
在这些拥挤肮脏的小巷子里散发出一种不太让人愉快的气味,一团人间繁忙的气象。
我们也是凡夫俗子,从来没有想超凡入圣,或者转生成什么贵人,什么天神,什么菩萨,等等。
对神庙也并不那么虔敬。
可是尼泊尔人对我们这些“洋鬼子”还是非常友好,他们一不围观,二不嘲弄。
小孩子见了我们,也都和蔼地一笑,然后腼腼腆腆地躲在母亲身后,露出两只大眼睛瞅着我们。
我们觉得十分可爱,十分好玩。
我们知道,我们是处在朋友们中间。
兽主大庙的门没为我们敞开,这是千百年来的流风遗俗,我们丝毫也不介意。
我们心情怡悦。
当我们离开大庙时,听到圣河里潺潺的流水声,我们祝愿,尼泊尔朋友在活着的时候就能通过这条圣河,走向人间天堂。
我们也祝愿,兽主大庙千奇百怪的神灵会加福给他们! 1986年11月30日离别尼泊尔前,于苏尔提宾馆 访绍兴鲁迅故居 一转入那个地上铺着石板的小胡同,我立刻就认出了那一个从一幅木刻上久已熟悉了的门口。
当年鲁迅的母亲就是在这里送她的儿子到南京去求学的。
我怀着虔敬的心情走进了这一个简陋的大门。
我随时在提醒自己:我现在踏上的不是一个平常的地方。
一个伟大的人物、一个文化战线上的坚强的战士就诞生在这里,而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。
对于这样一个人物,我从中学时代起就怀着无限的爱戴与向往。
我读了他所有的作品,有的还不止一遍。
有一些篇章我甚至能够背诵得出。
因此,对于他这个故居我是十分熟悉的。
今天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里,我却感到我是来到一个旧游之地了。
房子已经十分古老,而且结构也十分复杂,不像北京的四合院那样,让人一目了然。
但是我仍觉得这房子是十分可爱的。
我们穿过阴暗的走廊,走过一间间的屋子。
我们看到了鲁迅祖母给他讲故事的地方,看到长妈妈在上面睡成一个“大”字的大床,看到鲁迅抄写《南方草木状》用的桌子,也看到鲁迅小时候的天堂——百草园。
这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,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神奇之处。
但是,我却觉得这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。
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寸土、桌子的每一个角、椅子的每一条腿,鲁迅都踏过、摸过、碰过。
我总想多看这些东西一眼,在这些地方多流连一会儿。
鲁迅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他生前,恐怕也很久没有到这一所房子里来过了。
但是,我总觉得,他的身影就在我们身旁。
我仿佛看到他在百草园里拔草捉虫,看到他同他的小朋友闰土在那里谈话游戏,看到他在父亲严厉监督之下念书写字,看到他做这做那。
这个身影当然是一个小孩子的身影。
但是,就是当鲁迅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,他那坚毅刚强的性格已经有所表露。
在他幼年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里,我们看到了他用小刀刻在桌子上的那一个“早”字。
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。
有一天,他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,上学迟到了,受到了老师的责问。
他于是就刻了这一个字,表示以后一定要来早。
以后他就果然再没有迟到过。
这是一件小事。
然而,由小见大,它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省吗? 这坚毅刚强的性格伴随了鲁迅一生。
“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”,他一生顽强战斗,追求真理。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”他对人民是一个态度,对敌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态度。
谁读了这样两句诗,不深深地受到感动呢?现在我在这一间阴暗书房里看到这一个小小的“早”字,我立刻想到他那战斗的一生。
在我心目中,他仿佛成了一块铁,一块钢,一块金刚石。
刀砍不断,石砸不破,火烧不熔,水浸不透。
他的身影突然大了起来,凛然立于宇宙之间,给人带来无限的鼓舞与力量。
同刻着“早”字的那一张书桌仅有一壁之隔,就是鲁迅文章里提到的那一个小院子。
他在这里读书的时候,常常偷跑到这里来寻蝉蜕、捉苍蝇。
院子确实不大,大概只有两丈多长、一丈多宽。
墙角上长着一株腊梅,据说还是当年鲁迅在这里读书时的那一棵。
按年岁计算起来,它的年龄应该有一百八十岁了。
可是样子却还是年轻得很。
梗干茁壮坚挺,叶子是碧绿碧绿的。
浑身上下,无限生机;看样子,它还要在这里站上一千年。
在我眼中,这一株腊梅也仿佛成了鲁迅那坚毅刚强的、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的性格的象征。
我从地上拾起了一片叶子,小心地夹在我的笔记本里。
把树叶夹在笔记本里,回头看到一直陪我们参观的闰土的孙子在对着我笑。
我不了解他这笑是什么意思。
也许是笑我那样看重那一片小小的叶子,也许是笑我热得满脸出汗。
不管怎样,我也对他笑了一笑。
我看他那壮健的体格,看他那浑身的力量,不由得心里就愉快起来,想同他谈一谈。
我问他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,他说都很好,都很满意。
我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多余的。
从他那满脸的笑容、全身的气度来看,他生活得十分满意,工作得十分称心,不是很清清楚楚的吗? 我因此又想到他的祖父闰土。
当他隔了许多年又同鲁迅见面的时候,他不敢再承认小时候的友谊,对着鲁迅喊了一声“老爷”。
这使鲁迅打了一个寒噤。
他给生活的担子压得十分痛苦,但却又说不出。
这又使鲁迅吃了一惊。
可是他的儿子水生和鲁迅的侄儿宏儿却非常要好。
鲁迅于是大为感慨:他不愿意孩子们再像他那样辛苦辗转而生活,也不愿意他们像闰土那样辛苦麻木而生活,也不愿意他们像别人那样辛苦恣睢而生活。
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。
这样的生活鲁迅没有能够亲眼看到。
但是,今天这新的生活却确确实实地成为现实了。
他那老朋友闰土的孙子过的就是这样的新生活,是他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。
按年龄计算起来,鲁迅大概没有见到过闰土的这个孙子。
但这是不重要的。
重要的是,鲁迅一生为天下的“孺子”而奋斗,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。
这真是天地间一大快事。
如果鲁迅能够亲眼看到的话,他会多么感到欣慰啊! 我从闰土的孙子想到闰土,从现在想到过去。
今昔一比,恍若隔世。
我眼前看到的虽然只是闰土的孙子的笑容;但是,在我的心里,却仿佛看到了普天下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笑容,看到了全国人民的笑容。
幸福的感觉油然流遍了我的全身。
我就带着这样的感觉离开了那一个我以前已经熟悉、今天又亲眼看到的门口。
1963年11月23日写毕 奇石馆 石头有什么奇怪的呢?只要是山区,遍地是石头,磕磕绊绊,走路很不方便,让人厌恶之不及,哪里还有什么美感呢? 但是,欣赏奇石,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的审美情趣。
南南北北,且不说那些名园,即使是在最普通的花园中,都能够找到几块大小不等的太湖石,甚至假山。
这些石头都能够给花园增添情趣,增添美感,再衬托上古木、修竹、花栏、草坪、曲水、清池、台榭、画廊等,使整个花园成为一个审美的整体,错综与和谐统一,幽深与明朗并存,充分发挥出东方花园的魅力。
我现在所住的燕园,原是明清名园,多处有怪石古石。
据说都是明末米万钟花费了惊人的巨资,从南方运来的。
连颐和园中乐寿堂前那一块巨大的石头,也是米万钟运来的,因为花费太大,他这个富翁因此而破了产。
这些石头之所以受人青睐,并不是因为它大,而是因为它奇,它美。
美在何处呢?据行家说,太湖石必须具备四个条件,才能算是美而奇:透、漏、秀、皱。
用不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分析解释。
归纳起来,可以这样理解:太湖石最忌平板。
如果不忌的话,则从山上削下任何一块石头来,都可以充数。
那还有什么奇特,有什么诡异呢?它必须是玲珑剔透,才能显现其美,而能达到这个标准,必须是在水中已经被波浪冲刷了亿万年。
夫美岂易言哉!岂易言哉! 以上说的是大石头。
小石头也有同样的情况。
中国人爱小石头的激情,绝不亚于大石头。
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京的雨花石。
雨花大名垂宇宙,由来久矣。
其主要特异之处在于小石头中能够辨认出来的形象。
我曾在某一个报上读到一则关于雨花石的报道,说某一块石头中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像,宛然如书上画的或庙中塑的,形态毕具,丝毫不爽。
又有一块石头,花纹是齐天大圣孙悟空,也是形象生动,不容同任何人、神、鬼、怪混淆。
这些都是鬼斧神工,本色天成,人力在这里实在无能为力。
另外一种小石头就是有小山小石的盆景。
一座只有几寸至多一尺来高的石头山,再陪衬上几棵极为矮小却具有参天之势的树,望之有如泰岳,巍峨崇峻,咫尺千里,真的是“一览众山小”了。
总之,中国人对奇特的石头,不管大块与小块,都情有独钟,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情趣,为其他国家所无。
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香山饭店时,利用几面大玻璃窗当作前景,窗外小院中耸立着一块太湖石,窗子就成了画面。
这种设计思想,极为中国审美学家所称赞。
虽然贝聿铭这个设计获得了西方的国际大奖,我看这也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审美情趣,碧眼黄发人未必理解与欣赏。
现在文化一词极为流行,什么东西都是文化,什么茶文化、酒文化,甚至连盐和煤都成了文化。
我们现在来一个石文化,恐怕也无可厚非吧。
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竟在离开北京数千里的曼谷——在旧时代应该说是万里吧——找到了千真万确的地地道道的石文化,我在这里参观了周镇荣先生创建的奇石馆。
周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国立东方语专念过书,也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吧。
去年10月,我到昆明去参加纪念郑和的大会,在那里见到了周先生。
蒙他赠送奇石一块,让我分享了奇石之美。
他定居泰国,家在曼谷。
这次相遇,颇有一点旧雨重逢之感。
他的奇石馆可真让我大吃一惊,大开眼界。
什么叫奇石馆呢?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馆,难免有一些想象。
现在一见到真馆,我的想象被砸得粉碎。
五光十色,五颜六色,五彩缤纷,五花八门,大大小小,方方圆圆,长长短短,粗粗细细,我搜索枯肠,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带数目字的俗语都搜集到一起;又到我能记忆的旧诗词中去搜寻描写石头花纹的清词丽句。
把这一切都堆集在一起,也无法描绘我的印象于万一。
在这里,语言文字都没用了,剩下的只有心灵和眼睛。
我只好学一学古代的禅师,不立文字,明心见性。
想立也立不起来了。
到了主人让我写字留念的时候,我提笔写了“琳琅满目,巧夺天工”,是用极其拙劣的书法,写出了极其拙劣的思想。
晋人比我聪明,到了此时,他们只连声高呼:“奈何!奈何!”我却无法学习,我要是这样高呼,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。
听周先生自己讲搜寻石头的故事,也是非常有趣的。
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,一听到有奇石,便把一切都放下,不吃,不喝,不停,不睡,不管黑天白日,不管刮风下雨,不避危险,不顾困难,非把石头弄到手不行。
馆内的藏石,有很多块都隐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中国古书上说: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
”这话在周镇荣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。
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酷爱石头,有“米颠拜石”的传说。
我看,周先生之癫绝不在米蒂之下。
这也算是石坛佳话吧。
无独有偶,回到北京以后,到了4月26日,我在《中国医药报》上读到了一篇文章《石头情结》,讲的是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酷爱石头的故事。
王先生我是认识的,好多年以前我们曾同在桂林开过会。
漓江泛舟,同乘一船。
在山清水秀弥漫乾坤的绿色中,我们曾谈过许多事情,对其为人和为学,我是衷心敬佩的。
当时他大概对石头还没有产生兴趣,所以没有谈到石头。
文章说:“十多年前在朝闻老家里几乎见不到几块石头,近几年他家似乎成了石头的世界。
”我立即就想到:“这不是另外一个奇石馆吗?”朝闻老大器晚成,直到快到耄耋之年,才形成了石头情结。
一旦形成,遂一发而不能遏制。
他爱石头也到了“癫”的程度,他是以一个雕塑家美学家的眼光与感情来欣赏石头的,凡人们在石头上看不到的美,他能看到。
他惊呼:“大自然太神奇了。
”这比我在上面讲到的晋人高呼“奈何!奈何!”的情景,进了一大步。
石头到处都有,但不是人人都爱。
这里面有点天分,有点缘分。
这两件东西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。
认识这样的人,是不是也要有点缘分呢?我相信,我是有这个缘分的。
在不到两个月的短短的时间内,我竟能在极南极南的曼谷认识了有石头情结的周镇荣先生,又在极北极北的北京知道了老友朝闻老也有石头情结。
没有缘分,能够做得到吗?请原谅我用中国流行的办法称朝闻老为北癫,称镇荣先生为南癫。
南北二癫,顽石之友。
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,这样的癫是极为难见的。
知道和了解南北二癫的人,到目前为止,恐怕也只尚有我一个人。
我相信,通过我的这一篇短文,通过我的缘分,南北二癫会互相知名的,他们之间的缘分也会启发出来的。
有朝一日,南周北王会各捧奇石相会于北京或曼谷,他们会掀髯(可惜二人都没有髯,行文至此,不得不尔)一笑的,他们都会感激我的。
这样一来,岂不猗欤盛哉!我馨香祷祝之矣。
1994年5月24日凌晨, 细雨声中写完,心旷神怡 注释 [1]此文写于1988年前后,是季羡林先生晚年回忆1935年去往德国留学时途经中国东北一带的一段经历。
为体现事件发生时的时代背景,本文地名遵循原稿,未经修改。
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,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。
- 女为悦己者御井烹香
- 我凭本事伺候的老祖沙舟踏翠
- 女皇穿成林妹妹的那些事长生千叶
- 农女王妃:古代万元户江陌南
- 翅膀之末沐清雨
- 同学,你人设崩了江溪月陶夭夭
- 我的男友是厨神寻香踪
- 死亡万花筒西子绪
- 『』好孕小娇娘 作者:慕槿夕苏宁江阿木勒
- 『完结』《沸雪》 作者:雀七方幼宜纪临舟
- 连载至231《欲色罗裳》盛汝筠 薛轻凝薛轻凝盛汝筠
- 淫虐乐园BDSMFantast
- 饲犬(都市美食,年下1V1)鸣銮
- 梅子熟了欲心生
- 死遁后成为全员白月光 作者:岁宴君云青岫裴宥川
- 咸鱼躺平后爆红了[穿书]白荔枝
- 和校花妈妈之荒岛求生爱吃爱心炒面的木木
- 我曾是个传说[无限流]狂渚
- 富一代[穿书]山楂丸子
- 《星际第一人偶师》作者:白昼飞行收藏家宋白玉
- 《今日有囍》by长毛橘说道楚环
- 老夫少妻都是那颗苹果的错
- 重生七十年代做知青锦未知
- 无耻家族浪子刀
- 七玄苍鹤
- 她的娇软美柔南
- 无限治愈孤注一掷
- 成了禁欲男主的泄欲对象闻人醉
- 男配稳拿深情剧本[快穿] 作者:祝麟季眠的的小天
- 她有一个秘密(校园 1v2)小鱿鱼
- 实践教程偷马头
- 全家重生上娃综山多令
- 我将成神[无限]张无声
- 穿书渣雄被捡来的雌虫骗身骗心漫浪西东
- [补番]我杀猪养你啊(岁无鱼)楚火落蔺师仪
- [清穿同人] 清穿之侧福晋悠闲日常飞玉镜
- 五月泠明月珰
- 宠上眉梢乔燕
- 和离之后澹澹
- 《将军夫人是条美男鱼》作者:公子书生百里煊将军
- 重生1980:赶山致富宠娇妻骑驴看天
- 重生八零小农女三三
- 娇纵小漂亮总在渣主角[快穿]钓月迢迢
- 新婚夜,战神王爷红了眼笑轻狂
- 南雍王妃李木子子
- 听说我哥是暴君小姑娘太皇太
- 【完结】《不想卷科举,奈何大哥先躺平了》作者:九牛一毛岳知语不知道
- [主受]附加遗产[188团-虐文-双洁-HE-车全-番外全]温小辉秦子蛟
- 拼多多社恐逆袭(系统,nph)讲究人小李子
- [综漫]原来前任都是大佬柳箐欢
- 从霍格沃茨开始重新做人浓墨浇书
- 豪门案中案笑冶儿
- 娱乐:让你捡属性,没让你捡白露迷失自我的小僵尸
- 出狱即离婚,高冷未婚妻上门领证小蟹呀
- 让你基层干起,你转投进省委大院橙子你爱不完
- 觉醒sss级妖兽,美女老师抢着要同居山野村夫
- 万古神帝:都市弑神录轻狂书生小艺
- 透视:十万大山成了我的黄金宝库霹雳娃
- 一剑杀仙:从爆能系统开始笔落风荒
- 权力巅峰之官途正道焚情月下
- 香雪(帝妃、高h)晚风情
- 她的诞生(娱乐圈NP)木良
- Café Erotica盛肉不颠勺
- 拾花录(1v2 双舅舅 禁忌)来次熊抱
- 重生成偏执霍少的小仙女糖果淼淼
- 王令的日常生活枯玄
- 霍总,养妻已成瘾苏子欢
- 刘天仙的穿越老公盛夏读书
- 重生1985:15天赚了30万开滴滴的卢师傅
- 天道至尊驱魔师绯月天歌
- 誓不入宫门秦晓柒
- 落叶归根(ABO)画地为牢
- 山村美女图老婆爱我1
- 老舅别怕,十八个外甥保驾护航!序言
- 就算变身萝莉,也要大声说爱你墓色七凉
- 万事如意晏九九
- 娱乐:让你捡属性,没让你捡白露迷失自我的小僵尸
- 从女子监狱开始龙啸九州强仔很ok
- 高武校长,我的实力是全校总和!邯郸财阀
- 诸天降临时代,我的识海通洪荒墨子不语
- 博物馆实习生,开局被误认为邪神坚硬的豆浆
- 神农兰朗
- 千金归来洛云卿
- 重生都市之极品仙尊白夜买个锤
- 蜘蛛虽然弱却不是废渣大梦无常
- 垃圾异能不按说明使用它就是s级孤独老登
- 四合院:重生何雨柱,我坑死禽兽火龙果很好吃
- 穹天劫雨中小妖
- 潜规则之皇牛毛
- 重生官场,绝不当接盘侠淮左名猪
- 娱乐圈外挂光环梵辰
- 王令的日常生活枯玄
- 刘天仙的穿越老公盛夏读书
- 寒门崛起之从少校晋升将军最爱吃豆皮
- 学弟你选的,你闺蜜找我你哭啥!仆仆
- 被病娇姐姐圈禁?我反手PUA她暗烬歌者
- 世界首富之桃运渔夫酒级大眼木匠
- 重生之金融大亨崛起A金岭
- 全民地仙纪元仙寻道访
- 回春坊冬雪晚晴
![[更112] 叛逃之后(西幻nph) 作者:刁钻甲方在天堂(叠甲都叠成这样了请放过我版)](https://www.pushific.com/img/42578.jpg)